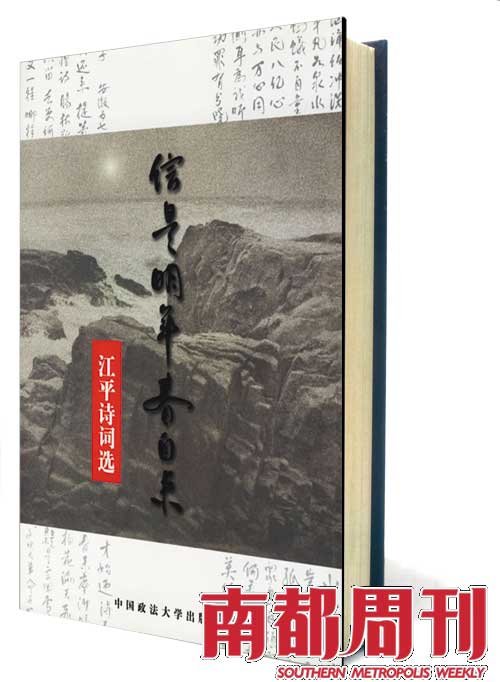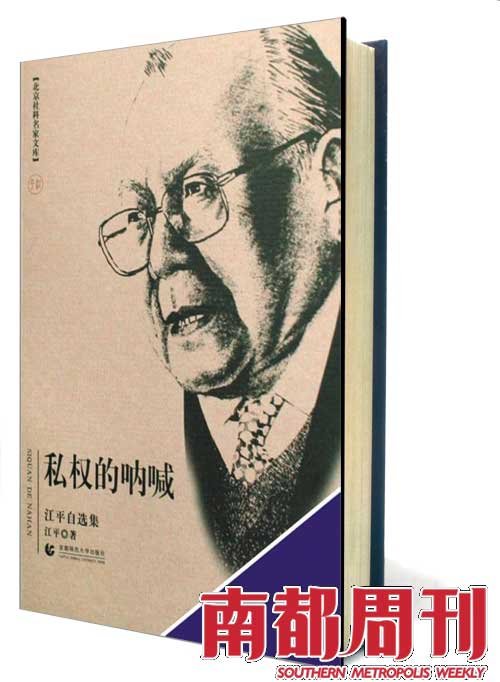| 您的当前位置: 首页 >> 热点文章 >> 文章正文 |
| 法学泰斗江平:只向真理低头 |
| 阅读选项:
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
| 作者: 来源:南方新闻网 阅读: |
[导读]一场大病让江平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现在看来,还是生命第一吧。”尽管如此,每每有关中国法治的重大事件发生,他依旧会在第一时间关心并郑重表态。 江平,这位中国法学界泰斗,用多舛的命运,见证并参与了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法治进程。他心甘情愿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从参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再到《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以及最近对“新拆迁条例”修改讨论的介入,他不停地奔走呼号,在一些被普遍认为敏感的问题上,经过深思熟虑后,认定“只向真理低头”的他总会挺身而出。而实际上,他又总是自谦为不是一名合格的法学家。如今80岁的江平似乎放慢了节奏,然而每每有关中国法治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他仍会在第一时间关心并郑重表态, 南都周刊记者_ 齐介仑 李颖娟 ( 实习生) 摄影_ 王旭华
残肢逆遇何足悲,伤情失意安得摧。 血泪是非应长记,桃粉往事莫须追。 盖棺文字不由天,迷津归力能回。 愿将惭怍五尺躯,送与世炉万般锤。 ——江平 江平这首作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七律自勉》,也许正是作为诗人法学家的他,八十载风雨如晦、岁月峥嵘历程里最生动逼真的人生写照。 江平对中国法治进程的贡献 江平从1986年开始,参与了诸多重要立法工作。
如《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信托法》等。 在《行政诉讼法》、《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中担任组长。有学者评价说,近几年私权在国内大张旗鼓,如论功行赏,江平居功至伟。 而在江平看来,自己倒是对《行政诉讼法》做了一些贡献。《行政诉讼法》作为中国第一个“民告官”的法律,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从实体法改到程序法由江平首先提出来。“民告官”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制度。 这两本书加上即将完稿付梓的40余万字回忆录,被江平视为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三本书。 一阵急促的吠叫声过后,一身淡黄色绒毛的小狗退回到门内,温暖平和的屋子里,飘散着淡淡的书香和花香。相伴10余年,这只来自日本的秋田名犬不能像从前那样每天清晨都准时陪着主人下楼,到河边和公园玩耍的机会也少了许多。 10年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购入这处位于北京南五环的房产,想借此避开一些邀请从而开始自己70岁退隐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任校长将终身教授的聘书送达,他盛情难却,不得不再次将工作变成了生活。 在媒体纷纷推出的2009年终盘点策划中,这位中国法学界泰斗,与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道,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十年影响力之民主法治人物”。 从《民法通则》到《行政诉讼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以及对“新拆迁条例”修改讨论的积极介入,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在多个重大社会事件处置和若干学术问题研讨中,他认真聆听并潜心研究,每每表达重要观点,老人蹒跚的身影、坚定的神情以及语重心长的表述总令人感动。这位仅仅任职两年就被免职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也成为学生心目中“永远的江校长”。 风雨兼程 祖籍浙江宁波的江平,1930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立志成为一名记者,但时局动荡,在大学第一年他即停课参加学生运动,1951年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自此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 1956年,因成绩优异,江平获准提前一年从莫斯科大学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却被划为“右派”,饱经伤痛,加之这一阶段婚姻失败、一条腿在工伤事故中失去,人生顿陷低谷。但他矢志不渝地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与这所后来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的院校相互交织,共经风雨半世纪,至今仍辛勤耕耘。时至今日,他已培养出众多一流法学人才,他的思想和人品更是熏陶了几代学子,影响波及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中国法学界公认的权威法学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从工作到生活,如今80岁的江平似乎放慢了节奏。 身材魁梧,略有蹒跚,精神矍铄,从卧室走出来时,老人轻轻地招呼保姆递送茶水。稀疏的头发基本上全白了,一副明亮的眼镜背后,目光和善而坚定,缓缓地坐在沙发上,他将庞大的身躯稍稍向后靠了靠,手臂撑起下巴呵呵一笑,不无自嘲地说,真是老了。从来没有服过老的他,2008年10月中风住了一次院,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按照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老例,前不久,中国政法大学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聚会,数百名各个阶段的师生好友纷纷赶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庆祝80岁生日。法学家贺卫方引用同样八十岁高龄的法学界闻人张思之的评语,笑称亦师亦友的江平先生自此步入“80后”。 江平喜欢狗。生病之前,每天早晨七点他就按部就班地起床去遛狗,家里一共养了两条小狗,都已十岁,前一段故去了一只,他为此非常伤心。老伴崔琦说,紧张工作之余,小狗也带给江平无限的快乐,每天,狗要和他一起睡,情同父子。 老伴崔琦76岁了,这位18岁就参加革命的前华北大学毕业生谈吐儒雅,除了学校安排的学术助手之外,她是江平最靠谱的生活秘书。 在这处300多平方米的住所,从客厅通往卧室的门廊上,江平亲手用毛笔写成的“忘忧”二字被嵌入金属标牌悬挂在正中。江平对老伴说,进到卧室以后,所有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一概忘掉。 除了一名保姆外,略有残疾一直未嫁的女儿江帆也同他们一起生活了38年,而这也是江平夫妇至今尤其牵挂的一件事情。儿子江波出生于1969年,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读完MBA回国创业,如今事业还算成功。 由于家族史等诸多原因,江平那次患中风后遗症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吓坏了众多学生。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医生的建议是,以后工作不能太紧张太忙。之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江平将所有在校外的讲课全部辞掉了,开始放慢工作节奏去完成手头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作息时间更加规律和节制起来:每天早晨8点钟起床,基本每晚10点半左右就休息了,不再开夜车。“现在逻辑也还可以,但刚出院的时候,我不太敢做学术报告,怕思维不够敏捷造成问题。” 病前,江平曾同时在北大、清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四家著名经济管理院校教授EMBA课程,是商法的主讲人。江平说,这次生病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现在看来,还是生命第一吧。” 法治布道者 尽管如此,每每有关中国法治的重大事件发生,江平依旧会在第一时间关心并郑重表态,他忘不了这个江湖。尤其在一些被普遍认为政治敏感的问题之上,经过深思熟虑后,“只向真理低头”的他总会挺身而出。 江平是一位始终独立思考而又乐观豁达的老人,从“反右”到“文革”,再到在特殊背景下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这些大大小小的挫折并没有泯灭他对未来中国的热望。人生虽已八十,精神不改,他的“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每每被念起,令人肃然起敬。 60年来,中国法治在曲折中不断进步,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三尺讲桌旁总少不了他法治布道的身影。 他时下仍然在招博士生和博士后,加起来也有10人左右。虽然身处相对偏僻的北京南城,远离校园,年岁大了、体力也不再如前,但每个学期,江平都要到蓟门桥给博士生们讲授两节重要课程,每次一个上午,前后四个小时。 除此之外,中国政法大学开学典礼以及其他各种重大活动,也必请江平到场,比如最近比较法研究院的成立。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届博士,迄今已经19年。在这19年的时间里,江平总计培养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目前,这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法官、律师等,谈及自己的学生,他欣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江平第一届博士生中的赵旭东,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商法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被评为中国法学会十大杰出中青年;目前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知识产权庭庭长的孔祥俊,在江平印象里是个勤奋的学生,也被评为中国法学会十大杰出中青年。“这都是我非常不错的学生,但我培养的学生,从事教学科研的比较多,当官的几乎没有,当大官的更没有。”江平说,现在很多官员都到学校去拿博士,但他并没有刻意去招些官员做自己的博士生。 在江平眼里,自己是一个喜欢讲台远胜于喜欢写作的人。而他的讲座,往往也是听者云集,一票难求。 这位精神领袖式的法学先驱,不仅在中国政法大学得到了师生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社会上的各种演讲、座谈也是邀请不断,哪怕只是15分钟的陈词,江平都需要认真准备上好几天。 他不停地奔走呼号,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发表观点。2009年,城市拆迁引发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江平,这位当年的《物权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中国重要财产性法律制定的领头人,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又出现在媒体上,面对凤凰卫视的采访谈到,要以法治化解社会纠纷,旧法何时废除是关键。 此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江平认为,我们的一部法律制定后,并不像国外那样同时宣布与其相冲突的法律或法条无效。而在多法并存的情况下,很多部门还是选择对己有利的法律执行。 除了仗义执言,在一些敏感事件里,也屡屡能看到江平为受害者请命的签字,为深陷困局的年轻人站出来给予声援。而他却总自谦为不是一名合格的法学家,充其量只能算个教育家,因为读书不够多,著作不等身。 要不要写回忆录 生活中的江平,是个铁杆球迷,这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崇德中学读书的时光,从那时起,他便是校足球队主力。一谈起足球,老人顿时表情丰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球迷是不是不多?”随即,他呵呵一笑。 2008年北京奥运会,江平专程前往工人体育场,观看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半决赛,之后又到鸟巢看了一场国际米兰与拉齐奥的对阵,大呼过瘾。 除了古典音乐、京剧之外,足球是江平最大的热爱,而国内的足球比赛,他也多有关心,但凡有国安的比赛,他便抽出时间盯着。老伴崔琦半夜醒来,经常看到他披着衣服在客厅看球,“那可真是球迷,如果说晚上还有一场比赛,哪怕半夜两点也要爬起来。” 崔琦说,当年在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江平就是校足球队的。后来被划成“右派”,那段时间心境沮丧,在劳动期间被火车轧断了腿,球不能踢了,就光剩下看了。 江平说,他不是文盲,是电脑盲。尽管家中有电脑,但并不懂得如何操作,他的生产方式还是手工作坊式的,他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不足。因为不用电脑,很多信息的利用就会受到限制,视野不够新、不够宽。不过,他又自我解脱说,好处也是有一点的,那就是,不会被网上的大量材料所淹没。“所有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是我思考后的文字呈现。” 人生要不要写回忆录,江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觉得有点意义,觉得好像可以留下点东西,但又有时候觉得很没意思,他发现现在写回忆录的人很多,“但写出来,真的有人看吗?”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领导曾经多次与江平沟通,再三坚定他的意志,并特别安排了一名学法制史的博士为他做学术助手,帮助他梳理材料并整理口述录音。 校方希望出版江平回忆录的理由是,现在,中国法学界经历比较复杂一些、磨难多一些、岁数又大一些的,江平先生算一个,而且从江平自己的立法工作来说,经验是丰富的,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做过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而这些东西写下来是值得的,于是一直鼓励他写下去。 “我坚持了一阵,自己写了十多万字,发现这个任务很庞大,要写的东西太多,好在有人帮我整理,我就省事多了,我看了这个小伙子的写作水平,很好。”现在,学校的意思是,希望他今年拿出这本书来。 江平认为,自己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三本书,除了《私权的呐喊》和诗词集《信是明年春自来》,第三本书就是这本回忆录了。 “我这个留给人间的回忆录,至少对中国法学界可能有点用处吧,现在学法律的人也多了,将近600所法律院校,学生里面知道我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留给他们作为借鉴,哪怕仅仅是开阔他们的知识领域、让他们知道一下中国法制建设苦难的历程也好。” 南都周刊——江平 “推动立法的力量不在个人” 南都周刊:这几年,您主要在忙些什么? 江平:从生活上讲,我的老年朋友历来不是很多,一个是性格原因,一个是身体不方便。 最近几年,没有科研项目,除了回忆录,也没有独自写书的计划。现在就是应对周遭面临的问题,比如前一阵有个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讨论会要我发言,最近又有人提出国家垄断与法制的问题,我就得思考。这些社会活动还不少,完全退出也不很合适。 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三本书,都完成了。第一本书是《私权的呐喊》,把我一生中比较精彩的演讲结集成册。第二本是我的诗词集,主要是我被划成“右派”的时期写的。人生大概只有在经历苦难之后,才能写出一些好诗来,在我过去22年的苦难时期里,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文革”十年,读了很多诗词和古典文学,也写了一些。第三本书,就是现在的回忆录。应该说,我留给人间的也就这么多了。 南都周刊:学法律似乎并非您的初衷? 江平:是的。1948年高中毕业时,新闻系是我的第一志愿,那时候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很出名的。实际上,我学新闻不到一年就出来工作了,到了北京团市委,1951年公费派去苏联学习。这并不是我能够选择的,学法律完全是当时国家的安排。我是中国大规模派到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 南都周刊:留苏期间,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江平:在苏联待了5年,“斯大林秘密报告”对我的触动最大。1955年,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报告,报告最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广播出来。之前大家都把斯大林当神一样对待,现在一下子变成杀人犯的样子了,心理冲击非常大。 南都周刊:这些年来,您个人认为比较成功的是做了哪些事? 江平:中国的立法很难说是哪个个人在推动,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个人觉得,我应该是对《行政诉讼法》做了一些贡献,倒不是《民法通则》。我后来做过《行政诉讼法》立法组组长,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从实体法改到程序法这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中国第一个“民告官”的法律,而“民告官”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制度。 (南都周刊) |
| 【大 中 小】【关闭窗口】 |
|
|
|
|
|
|
|
| ·昆明市领导干部职务分工.. ·新版律师执业证编号规则 ·湖南永州一男子闯法院枪..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身..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律师到底能挣多少钱? ·许思龙律师简介 ·有收条就能证明已付款吗.. ·深圳、广州、厦门三地律.. ·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表20.. |
|